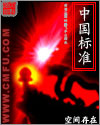标准后母-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亏她说得出口。“那你毁了她一件衣服准备赔多少?”
“我……我哪有……”她眼神闪烁的否认著,不相信他眼睛那么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给她机会自首。
死不承认是防身手册第一则,她自编的。“你要诬陷我好赖帐是不是?!”
“慷文,你的固执和你手上的瓶子一样害人。”他倏地抽出她一直背放在後的左手。
“噢!”他真厉害,该不该写诗歌颂他。
“只有噢吗?你要不要解释你顺手泼出去的东西是什么。”霸气 书库 提供他说得很轻松。
一瞧见两人的神情,他心里便有谱了,这一大一小最擅长狼狈为奸,可只要对象不是他倒无所谓。
所以他冷眼旁观其一举一动,问云用力摇晃可乐罐的狠劲不难猜出他的用意,但他没想到他会暗藏蚯蚓在身後,而且准确无误的平均洒在尔西及嘉丽身上。
当然他也没有错过在可乐喷出之际,同时有道小水注射出,未及时揭穿是想看看她到底有多坏,能睁眼说瞎话的力表自己的无辜。
事实证明她坏得没有一丝愧疚感。
“没什么啦!不就是一些肥皂水、醋啦!无伤大雅。”合起来叫化学物质。
“噢!”为什么他听起来像有什么?
“你别学人家乱噢,我对谋财害命没兴趣。”死小鬼、臭小鬼,居然没义气的先溜。
“你确定没杀伤性?”他引诱地轻触她的唇。
化学物质怎么可能完全无害?只是看是轻是重罢了,可是她绝对不会告诉他,她刚洒出去的到底会让人怎么样。
“你想吻我就吻吧,反正我已经被你吻得没什么名声了。”她正气凛然的决定牺牲。
“不,我比较想……”他眼神轻邪地盯著她胸部,然後……“打你的屁股。”
“嗄?!”
夜,适合做很多坏事。
轻叩的敲门声让刚洗好澡的滕尔东微颦起眉,随手拿起一件长裤套上,并找了件长袍披好。他不想引人非议。
因为他知道来者绝非害他洗冷水澡的人,她一向用脚踢门,踢不开才会劳动千斤重的玉手开门,然後埋怨他没事干么锁门,她绝对不会趁机摸上他的床。
相反的,是他想摸上她的床。
那个害人的小妖精真是狡猾,一听到他要惩罚她马上蜕身为水蛇,柔若无骨的缠偎上他怀抱,两脚勾住他的腰做出十分挑情的动作。
虽然以前的他称得上寡欲不贪欢,但自从遇上她之後,却成为时时充满兽性的欲望狂徒,只要她眼神或手指小小的撩拨一下,他全身的温度会立即窜高,渴望拥有她。
只是她像蛇一样滑溜,火一点就赶紧开溜,留下他一人饱受欲望的折磨。
若有下一回绝不放开她,先把火灭了再来谈挑逗,他有的是体力和她纠缠,燃烧一整夜是她自找的,放火的小孩会被火吞没。
“姊夫,我打扰了你吗?”
猛一回神,才开门的他眼神倏地一厉。“嘉丽,你不觉得穿少了一点?”
勾引他的把戏得向小妖精多学学,她的轻媚点到为止反而让人更心痒难耐。
“我……呃,我是想来向姊夫拿些止痒药。”她看来有些含羞带怯,但一身性感睡衣掩饰不了她的大胆。
“止痒药?”这是哪一招?
手一抬,睡衣肩带微微滑落。“洗了澡之後忽然全身发痒,实在是痒得受不了,才来问你有没有止痒药。”
“我没有止痒药,也许你去泡泡热水会好些。”她的肌肤上果然有细微的抓痕。
他大概知道慷文口中的没什么是什么了,她是化学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随手调制的整人材料必是不差,绝对如她自己所言的“无害”,只不过让人奇痒无比,没伤也会抓出伤,此举比直接朝人体泼洒有毒物质还恶劣,她真是坏得令人忍俊不已。
亏她想得出这么恶毒的整人诡计,难怪号称小恶魔的儿子也栽在她手中。
“没用的,我现在就痒得难受,你帮我搔搔好吗?”她娇媚的推落肩带,露出浑圆酥胸。
退了一步的滕尔东以不伤人自尊的口气道:“你很美,但我不想让亡妻以为我亵渎她的妹妹。”
“那你就当我是姊姊吧!她不会怪你的。”她一步步走近,身上的睡衣滑落在地。
“可是我的良心会知道,我不能违背道德规范。”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道。
文嘉丽眼露爱意地将手放在他胸口,“我爱你爱好久了,我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给你。”
“你喝醉了。”他刻意的一闪,避开她几近赤裸的惹火身躯。
幸好他事先洗了冷水浴,否则就糗大了。
“你明知我没醉,我只是想让你拥有我。”她似搔痒难耐的揉搓起胸部。
她身材的完美比例的确让男人无力拒绝,但是心上人就同住一屋檐下的滕尔东可不敢妄动,心态不定的小妖精很可能会在他的“宝剑”上涂上使其不举的化学物质,那他可就“永垂不朽”了。
“嘉丽,回房去,别让自己难堪,我不会碰你的。”他拿起床单抛向她。
“你会要我的,你是男人。”甩开床单,她做出挑逗的动作媚视著他。
“可是他是同志呐!怎么要你呢?”
一听便知是忍笑忍得很辛苦的声音,没好气的滕尔东拾起床单将文嘉丽包得密不通风,一手拉起蹲在门边偷窥的小偷。
她偷走他的理智,偷走他对女色的欲望,也顺手偷走他的心,但她却都不肯负责地矢口否认她是贼。
“你……你到我姊夫房里干什么?”就差一步就成了,只要她不出现。
看好戏咯!“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
滕尔东嘴角含著笑,怜悯她的飞蛾扑火,他正打算换张床睡,而且床上有她。
“我……我是来拿止痒药。”她现在才发现这个藉口十分蹩脚。
“我也是耶!”周慷文故意东抓西抓好像很痒。
“姊夫没有止痒药,你可以走了。”文嘉丽口气一恶的下起逐客令。
“不行,你都还没走。”笑话,我看中的猎物岂能让给你。
“为什么我要走?”她富家女骄纵的一面不意地现出。
“先来先走的道理你不懂呀!你一定没上过礼貌课。”看来她剂量调少了,下回加倍。
痒死她。
“我不走,你才是应该走的,这是“我”姊夫的房间,一个拿人薪水的保母没资格进来。”
她特意强调的“我”激怒了周慷文。
对喔!她薪水还没拿,怎能做白工。“很快他就不是你姊夫了。”
而且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周慷文拿起冷气机的遥控按了按,让室内温度急速下降,然後她神情自在的走向情敌。
“你要干什么?”文嘉丽防备的拉紧床单。
“没什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只是不想你著凉。”她用力一扯,扯掉了那条用以蔽身的床单。
“你……”
“好走呀!别太感激我。”周慷文做了个送客的手势。
冷气口吹出阵阵寒风,冷得难以忍受的文嘉丽全身打颤,双手环抱著身躯怒视著她,眼底有两簇毁灭的火焰,那是复仇之光。
她绝不认输。
第八章
“啊——你这淫魔在干什么?”
喝!听她嘴多恶呀!
一手探向她小腹的滕尔东巧施力道将她压在床上,一手按住她挣扎挥舞的拳头,眼泛欲望地吻住她,省得她喳喳呼呼。
爱玩火的人终将遭火噬,反扑的力量是她始料未及。
轻逸的嘤咛声很快地加入粗嘎的喘息声,她是欲拒还迎地霸住他的唇,野性十足的不让他占便宜,该采取主动攻势的人是她。
她想起白雪公主故事里的坏皇后,应该也是如此狂野的“攻击”国王,所以国王才会傻呼呼的任凭她掌控,连女儿不见了也不知情。
这么把自己交给他对吗?好像少了一道步骤。
“噢!疯女人,你干么咬我喉结?”是用牙齿咬而非挑逗。
周慷文得意的推开他。“咱们先好好的谈一谈。”
“在这个节骨眼上谈?”他忍不住瞪她,一股热气往胸腔烧。
“当然咯,不然要等到你兽性凌驾理性之上後再用身体交谈呀!”她可不是被爱冲昏头的小女生,她有脑子。
“我个人比较欣赏你最後五个字。”用身体交谈,他目前迫切需要。
“你野兽呀!光用下半身思考。”拧人要挑最痛的地方。
他的耳朵。
喔!她真会浇灭男人的欲望。“别忘了是你先挑衅的,我不过反驳而已。”
“我哪有挑衅,本小姐纯洁得像新生贝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他是个同志所以没法要你”,这句话你不陌生吧?!”翻了个身,他与她眼对眼地相互凝视。
装傻的眨眨眼,她以鼻子轻触他的鼻子。“我救了你耶!”
“要不要我以身相许,女侠。”他大手已经乐意的伸向她的腰。
“要,不过呢……”她的“不过”阻止他心中生起的欢喜。
“麻烦你一次说完别分上下集,我是具有人性的男人。”而且拥有男人最容易犯的错。
性冲动。
“你别不耐烦嘛!忍耐是一种美德。”哎呀!他的贼手在干什么?
是哦!她说得真简单。“你没听过忍无可忍毋需再忍吗?”
男人在欲望高张时是不可能停得下来,除非生理机能有障碍,否则她的要求简直难如登天取月,一不小心会粉身碎骨。
而他是再正常不过的男人,面对常常撩拨得他不能自己的美丽胴体,他若真能忍得住,才该怀疑自己的性向是否如她所言是个同志,他绝非圣人。
想他渴望她多久了,如今她人就在他身边、他的床上,不去尝尝味道有点对不起自己。
“尔东,你好像欠了我一样东西。”不讨回来是她吃亏。
一听见她柔柔地轻唤他名字,滕尔东心酥的想给她全世界。“什么东西?”
“钱。”
“钱?!”他有一瞬间的迷茫,好像在云层中踩到小石头。
“对呀!我的薪水你还没给我。”亲兄弟明算帐,何况他们只是未来的同林鸟。
遇到大难还是会各自飞的那种。
“薪水?”神智降落在地面,但仍有一丝迷惑。
“喂!大老板,你不会想赖掉我当保母的薪水吧!”他干么像鹦鹉似地老是重复她的话。
有付出自然有收获,她可是非常认真的尽忠职守,把小恶魔磨成未来的魔头。
功不在高,有灵就好,劳不在深,钱子拿来。
他错愕的睁大眼,“你在这时候向我要薪水?!”
她脑袋瓜里到底装什么,该抓她去实验室解剖研究,她大脑构造肯定异於常人。
“一个月又五天七个小时,我允许你先付一个月薪水。”小老百姓是靠薪水过活。
“请问七个小时是怎么算的?”五天他能理解,还是她薪水是算时薪的?
“呃,这个嘛,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嘛!”问这么多徒惹伤心。
“慷文——”他声一沉地在她腰上施压。
不能明说的时候一定有鬼。
“我是怕你儿子一个人睡太寂寞,所以帮他想了个助眠的法子。”她是乐於助人,小马哥应该颁给她一面奖章。
“你们又合谋整了谁……喔!我知道是谁了。”他该不该头痛找错保母?
本来是照顾、看管小恶魔,谁知竟请来了恶魔导师助他早日成魔。
说不定哪天她一时兴起开了所恶魔养成班,魔化全市的小孩。
“怎么,你心疼呀!”她嘴上含酸的一噘。
纵容两人“行凶”的他好无力呀!却不内疚,“先说说你用什么方法整嘉丽?”
“也没什么……”
“别又说没什么,我一听你说没什么就心惊胆战,你直接告诉我结果。”他打断她的话,暗自呻吟。
“没什……好嘛!别瞪人,我说就是。反正她爱脱衣服,我就让她不用穿衣服……”成全她的暴露狂。
她只是用了一桶快乾放置在无色的化学薄膜上,再贴在床单让人完全无从察觉,而人的体温会慢慢地融解化学薄膜。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再辗转难眠的人也会难敌睡意的沉沉睡去,快乾便会在此时渗出薄膜黏上任何布料。
“放心,不伤人的,我在快乾里加入两样小东西,使其不致黏上人的肌肤,顶多像是青春期的少年。”看吧!她多学以致用,看谁敢再说她不务正业。
“我几乎不敢问你话里什么意思,麻烦你不要告诉我。”他爱上的是人吗?
可是她爱和人唱反调。“青春痘而已,有点像水痘布满全身。”
“天呀!我真该把你和问云隔离,你一定会带坏他。”不,应该说已经带坏了。
“哈!你在说笑话吗?你儿子不用我带就很坏了。薪水快给我,支票我也收。”她好像没和他谈到薪资多寡问题。
“明天给你。”此刻他心脏跳得厉害,需要一点抚慰——用她的身体。
不过她也懂得谦卑,“我能问你一个月付我多少薪水?太少会显得人缺乏诚意。”
物极必反,人一旦在同一时间遭遇到数件难以负荷之不可思议的事,磨粗的神经自然而然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