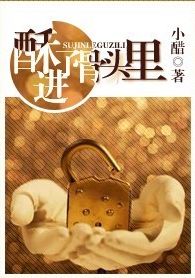������ͷ������-��2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ظ���ʱ��Ҫ�Ų������ӣ����費��Ц���㡣�ҼҴ��ų������Ż������㡣
�����Ҷ��Ż�Ͳ������Ц����˵���������Ǹ�հԶ������������Ƥ�۹ǡ�
��������Ȼ���ҵķ�����Ϊ�����������´ʵ�������������Ц�����춼û�ã���˭Ц�����
������������ͷ��������֮ʱ�����һֱ�ڷ���̽�ա���־����Ŀ��ͣ����ijҳ��ͼ�ϣ��ٳٲ��ơ������ֻ��Ҵչ�ȥ����һ�鿴�������һƪ�ģ���ͼ�Ǻ��������ĵ���һ�����ư�ɽ��ˮ��������ô���������
��������֪Ʈ������ȥ�˵�˼�����Ҳ��˻�������ӵ����һ�𣬡����������ô������
�������ù���־�����˷�ǰ��ҳ�IJ�ͼ����������������Ҫ�½��ۣ��ǵ������侳�������ij���Ƭ������ʹûPS����Ҳ�������ģ��Ų��á������������ҿ������֣������Ǵ˵��غ�ƽԭ�ϸ�������չ��ƽ�⣬��Щ�ضμ����������̣�����ˮ��Ȼ�������������ƣ�ȴ�Ե���A����½���������Ϲ�ҵ����������羰�������ĺ����ߵȼ���������Ȼ������������ҵ���д�ȫ�濪������������˶����ƾ�������ơ����ɴ˿ɼ�������ض�����ҵ������ƺ��൱ֵ��һȥ����
�������š�������ͬ����Ц�Ƶ�˵����ɣ������͵��ȥ�Ƕ�������ɡ���
����������������������ʱ����������һ��С���£��ܾ��ˣ���ȴһֱ����ؼǵã����Ե�ϲ����
������˵һ��Ǯû�еĸ�����һ������С���϶ȼ٣�������ɳ̲����ԡ�����⣬����������ƣ��������º��磬�����Ŵ���������������������ʳ��������������Եĵ�����һ������Ľ�Ұɣ���������ֵؿ�������������Ľ��ʲô��������˵�����ҿ�����ÿ����ڶ�����˽�˷ɻ����������ĵ������������õ�һ�С�������𣬡�����ɶ����Ľ�ģ���һ��������ʮ���춼������������Щ���顣���������
�����Ұ��������˵������������һ�䣬����λͬѧ������ʮ���������ȥ�������۲���ȥA�����¸�͵����ôΣ�յ��¶����۾�ȥƽ�Ȼ�������ʵ������������С���
�����������ò������������ŵ�ң������Ƿ�꣬���ְ���־�ӵ����ϣ����½����һ��һ������ȥ�ҵ��·�������շת��
���������������ļ��¡�
�����붬֮�߷��Ѳ��������ǵ����ȵ�ʱ���뵽���⣬������ϰ�������ǵ���������֮�ˣ�Ҳ���ѿ��������ǵ�֫������ʽ���������Ը������Ż����Ǵ�̨�����ż��������ף��봲�������ij�����繣��γɿ������������Աȡ�
�����������ܼ�ֶ������һҳ���鲻�࣬������������һ�������ϵ�٩�������Ķ���������ۣ���ҪƷλ��Ҫ������������������ȤҪ�ӡ�������ϸ���������̫���ܾͲ���ϸ�壬Ʒλ��������ǰ��������ʹҴұ����֡���һ����ߡ���������Ȥ���ԡ��ִ��Բ�֢�����ٶȡ�Ϊ�ף������������������Խ��ԽԶ��������һ�����ڽ����ߣ��������Ż���һ�����飬����һʱ�벻���������������Զ�������������һ���������Ǹոշ�����һ���������£��������������죬�ƺ������ٶ��������룬����������ˡ����ٶ�ʹ���ǽ��������������˻�����������
�������ٶ��Ǽ�������������������Ϊ���ֵġ�Ħ��ʱ����ʹ���Ц�����м���ȥ��������ʮ��ǰ��ĬƬ�����������⣿Ҫ���������ҵ������е����ϸ����һ���ᳫ�죬һ�ж����ٶ���������ʵ�֣�ʱ�䱻�и��һ�������ĸ���˲�䣬�����е������Ǵ�Ƭ���ס�
����������ٵ�ʱ����Ҳ�������Ǹ���������ʱ������
���������Ȼ����ʱ����ʣ�������Ķ�����֮�����֮һ�����ô��Զ����������ۣ�ÿһ����������˼����ÿ������������ÿ��������Ʒ����ÿ����Ϣ�ǻ�ζ��ÿ�����Ƕ������ǣ�ÿ���ߡ��������ڻ��ͨ��������˹���أ�����һ�����͵��������ÿ�����䣬���Ტ�á��Ƿ����������̽���һ�ѻ��������ҵľ��������У��ҷ��������ֵ��죬�ڱ̺��˼��Ϸ����š�
�������ˣ��˻�����繡��ҷ��˸���������������
�����������Ĥ�������Ӷ���������������һ·���£����ǣ����ţ��������������ͣ�������١������������̡���Ӳ�����������������۵Ĵ��У��Ұ����Ϳڣ�����������������˱���������롣�Ϸ������������ŵ��������ǽ����������ɫ�������������黰�������Ҷ�Ĥ���������Ժ��������ҹ�ͷ��ֱ��������������ο��
������������ɲ������ͼ�ÿ�������ֹס����ζ������������һ���ᣬ����ϲ���ý���û�н����ϣ������ȴ���ó־ö�����ʮ�㡣��������ƽ���������߷�Ҳ�����ˣ�����ſ�ڵ��ϣ���ֻ��һ��������
������ƽ�ⱻ���һ���ʾ���Ȼ���ƣ�
��������Сʱ�������������������������ǵİɣ���
������
������Խ��Խ�䣬ѩԽ��ԽƵ��·���ı�Խ��Խ�����ü�ʱ�����������Ħ��ȥ�ϿΣ����ܲ����ġ���������Ϊ�⣬Ц˵ȥ�궬�����ô�����ģ��������⡣�����ﵽ���Ľ�ѧ¥��������ϣ���·ȴҪ������Сʱ��������������������ȴҲֻ��������ȥ�ֻ�������ڼ������ʱ�����ⵣ�ǣ�ÿÿ��������ɲ����IJŷ��¡�����������̨�ϻ���Ļ����Щ���ڴ�̨��ʱ�������ȴ����˹�����Ů�ӵ����飬�����Ҳ�������˰���
����ż��Ҳ���ڸ��亮���д��߷ɳ�ȥ�������˳��ȥT���ŵ����¿Ρ��ڽֱ����Ⱥ���������Ŀ��������߷��ƺ�����ϲ����ֻ����β�ͱ��Q�����Լ��ߵȱ߳ԣ���һ������һ����ů�ͺ͵Ķ���ȥ���������������ף�ٲȻ�»�С���ڶ���
�������ǽ����Ѽ����վ��������ҵij����ѽ�����ȣ����˳��㳤������ʳ�ͻ�������һ����һ���Ƚ��������IJ�һ����һ����������ѴӼҳ���������Ͳ͡����������֮������������ÿ�ٶ�˵�������Թ�����óԵIJˡ��Ҿ�����������һ���أ����ֶ�ˣ���𣬶��óԣ�������óԵġ����Dz���ݸ尡��һ�ʾ�¶�ڡ������͵�����������������Ŀ϶��������ŷ�������ġ����������С������������¶¶��ϯ������糱�������˺ö���Ƭ���˵ģ���ģ��ŷ���¶¶�ģ���Ը�����á�
����ȥ�����µ����Σ���β��������ˣ�ֻ���������������������š���֯���š���ë�£��������ʾ��ͼ�治ͨ�ף����������ƽʱ����ͼ��Ǯ���˶����˺ü��黹û��������ô���Ʋ��ԣ������ǽ�����ѧϵͬѧ�ĵ㲦�ҲŰ�ë�߹�����ȷ��ԭ����ʹ����ͥ��ŮҲ��Ҫ���õ�3D˼άѽ���������϶��Ű��룬����ȴ���ǹ�����������·����ˤ�ţ������о����������������Dz�����֯��֯���ִ��������ٲ���˷������ұ���ŵ˵���������ǰ�����Ⱞ������ůë�£�������۳���Ԫ���ˣ�����������û֯���������������͡��������Ǹ�Դ˺������Σ�����ĵ��Ƶģ�ʱʱ���Ҹ��£�������ɶʱ����ᣬ�������ٶ���ҪЩ���ӣ���ȴ��������в�ң�����˵����ٴߣ��ٴ��Ҿ�ͣ����ֱ�ӽ������̳������У����㰾�����µȽ�֡�
�������ӹ�ů���㣬��ȴ��û�ܹ���庮����ҹ����DZ���һ�������ȵ��������뻳����ů���ӣ�����˯ǰ����һ�£����ڵ����˵����Ӷ�ð������������˳�ƽ�����һ�𣬱�˿���������䣬��ҹ���ߡ�
�������������������յ���������ף�Ƥëһ�壬���汣ůʵ�á���������˵�������������ҵ��������ˡ���
������Ҫ��ô������
���������������治���ף�������֪���ʣ���
��������Ȼ����֪���ʣ���������˵����
������û�ޣ������ۣ���Խ��ij�˰���Խ���¡���
�����������ù���ȫ������Ƥ����˫��������͵���֡�
������������������͵ع��ţ����������˲�������ȴ������ץ���������Ϊ�����Դ�һ·������ȥ���ⲻ֪���ܲ�������������ʡ������ú����ٶȻ�����һ��붬������ʱ��������̾�ù⾰Ϊ��ֻ��һ���ض��ݣ���ϡ�־�������������Լ���������������������ˡ�
��������
�����Ҷ�������·���ĵ��Ĺ�Ȼ���Ƕ��ࡣ
����һ�µף�һ���糣�����磬�������˷��糣�ȸ��������ȴһֱ���ûţ���ͼ�ܱ���ë���ܴ��룬�߷����ҷͣ�һ�ж����糣�ز��Ծ����������¿�����һ��Сʱ������ʮ���Ӿ͵��ң�����ȴ�ٳٲ����ˡ���ҹ�������ڵ�����������������ߵü���������ͷ���ڼң�����˶�����������
�������ֻ�����ͷ�ִ����й��ƶ����������е��û��ѹػ����Ļ�еŮ������ǰ��ʮ��һ�����������Դ��¿ξ�û���������˳������ˣ��ҷ���Ҳ�ѳ��״��ң���������ס�������·���ȥѧУ������
������ѧ¥����ͷ�ܶ���ѧ���Ƕ�����������ͷ�ڿΣ������Ŀα�����ʱ������û�εġ��ҽ�סһ�ˣ�����ѧϵ���ĵ�����ס�ĸ����ᡢ��ô�ߣ�֮�������ָ������ȥ��¥�´����ҵĴ�үһ�߲鿴�����ᣬһ�����ң�����϶���˵��������������ģ�����ô����û���������ְ�����¥�ﻹû���Ҳ���ʶ�����ء���
��������Ҳ��ȷ�����������ѧ���ĵĶ�ס������Ǿ�û����������ʶ��������Ϊ����סУ������ү���м��¶�����Ҫ���Ҳ�����������һͬ���ѧ������Ҳ�ɡ���
������ү���˸��ţ����˸����������Ӻ�һ�����߹������ң������Ҹ����
�����Ҽ�æ��ͷ����������ͬѧ����
�������ǰ���������ס�������ûס��У����
��������֪�������ҵ�Ȼ֪��������������Ͽ���ô����
������Ӵ�����һ���ûע�⡣���������ң������ǡ�������
�����������룬��֪�������������Լ����������ô�жϣ�˵����Ů���ѿ��и���Ӱ�죬������˵�������ˣ����������ˡ���
�������ޣ������ͳ��ֻ���������°��������ʱ��ˡ������ӵ绰¼�����˸����֣���ͨ���DZߴ������Ů�������ֲ������������ݡ�
������XX�������������Ͽ���ô������Ŷ����֮���أ�����Ŷ����Ŷ���ã���֪���ˣ�л�˰�����������ͨ��������˵�������ˣ�������ôȱ�εģ����Ǻ��ٸ�����һ����Է�����ͬѧ˵���¿�֮�����Ħ�����ˣ���ƽ��һ����Ӧ���ǻؼ��˰ɡ���
������Ȼ����ѧУ���£����������ĵ��ֽ���һ������������л��ȥ������������ʵ���벻����һ������˭�ˡ�����ɶ����ֱ����ʱ�����٣���ʱ�˿��Ҳŷ����Լ���û���κ�����ʶ���˵ĵ绰���������ѻ��Ǽ��ˡ���������һ���־��ü�����Ҳû�ã������Ǻ�������һ�𣬱ض�����Ҵ�绰����������һ֣̿��ο�������һ����ô���ˣ���û�������ᵽ���ĸ����ѣ�����Ǽ���û�С�
�������������Σ����벻�����dz������⣬�����������������Կ��ܡ�ԭ·���ҷ���â���ڱ���
������·�ֲ���N�κţ����һ�ξ�Ȼͨ�ˣ��绰��ͷȴ�������������Ǻ����ס������ڿڣ��Ҽ����̵̻ؽУ�����������
�������и���ǰɡ�����λС������������á���
������ʲô���ã������أ����ǡ�������
�������������Ժ�������ձ��������������ţ������������ֻ����������˵绰�ء���������������Ļ�����һ�˰ɡ���
������
����Խ���ļ����Խ�ǵ��飬��Զ��·��ƫƫ�³�����һ·����˾������������ҹ��Ƶ���ҽԺ��ȴ�Ķ�û�����Ӱ�����������ʵ��˸��Ҵ�绰������λ��ʿ���ҵ�ʱ������æ����ҩ������߶���˵������С���Ӱ��������˸���תԺ�ˣ�ǰ�Ŷ�����û��������
����������ô����ˤ����ô���ϲ����أ�������ô����Ѫ��ô����
��������˼����������ϰ���һ��������ʺŵģ������������ˣ�Ц����С������Ƶ�˵������������������ؽ��ѷ���С���ۣ�������ʲô�����⣬����ļ����������ѹ������Ѿ�����
������ת�ĸ�ҽԺȥ����֪��ô����
����������һ�������ֲ��䣬������������ͷ��С�ɣ����������������ٶȣ��Ǽ��ơ�����
������лл������������˵ʲô����һͷ��ˮ������Щ���ڶ�����Ҫ����ֻҪ�����ҵ�����Ҫ������ƽ����ת������¥����Ժ��������ſ�һ������������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