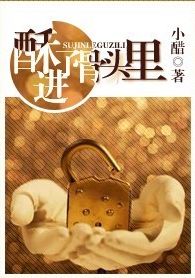穿过骨头抚摸你-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不对,不对,你刚才说的是……是……”
“我说我爱‘你’。”他的目光仍然投在我看不见的高空,仿佛他真的能看见那里有浮云。
K,这人绝不是新手,绝对不是。这话题转移得好,转移得秒,转移得我无言以对,只能僵在那。
我告诉自己,镇定,然后我使劲振动胸腔,弄出一个笑来,笑得肚子上的他的脑袋也跟着颤。我说,“小朋友啊,虽然男的几乎对每个跟他上床的女的都说这三个字,可这并不代表你也必须说,也不代表每个女的都想听,比如我。”
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我这样叫他,也不看我,自顾自地说,“我是认真的。”
所谓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一定就是他这种。我笑不出来了。
麻色窗帘突然飘起来,有穿堂风溜进屋里,带着月季花香,抚过桌上的茶碗,散落的书籍,年轻的身体,成熟的身体,躁动的心,尔后从后门悄然离开。
“你相信一见钟情么?”他把我从对风的追随中扯回来,“就是,你一看见这个人,你对她一无所知,她做什么,她什么性格,她的喜好,她的姓名年纪,这些都不重要,她身上就是有种东西一下子就吸引住你,绝不只是外表,她的身体里面好像有力量无形中控制着你,让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让你失了魂。”
我从前不信,可遇见你之后,我信了。就是这样的描述,把她统统换成他。
可我没说话。我不能说出我信。他年轻,不懂事,被激情蒙着眼睛,看不到现实。我和他的差距,不只是年龄,更致命的是我的过去。每个人都有过去,可我的被打上了标签,我必须接受众人诘难目光的洗礼,而少不经事的他,显然不适合和我并肩而站。
我静静躺着,眼角有液体滑下去,滴到他的枕巾上——印着北京市第几毛巾厂的那种。我答非所问,“你自己住?”
他更答非所问,坚持自己的路线,“你不相信?你觉得我的话可笑,是么?”
好,那我换个方针,呛他道,“你都没交过女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爱么你?你这叫什么你知道不?少年不识爱滋味,为赋新词强说爱。”
“你看过骇客帝国没?”
耳熟,“特有名一片吧?没。我很少看好莱坞。你想转移话题是怎么着?”
“我也从来不看这种片,这是有次陪别人看的,片子讲什么我都忘了,可里边有句话我到现在还记着,就是先知对内男的说的一句话,他说:‘你现在不知道爱是什么,可它到来时,你从□到骨头都能感觉到’。”
“……”
他翻过身来,右耳和脸压上我的肋骨,目光找准一个角度绕过乳房来,纠缠住我的,“遇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那天,我何尝不也是。虽然我没那个丸。
“你哪年的?”他的手指顺着方才阻碍了他视线的圆润轮廓,划至顶端,盘旋着。
“比你大三岁吧,24了。”意识想推拒,身体想迎合,二者交战中。
“挺好。”他定住捏了一下。
算了不纠结了。过了今天,可能都不会再见面,要珍惜当下。现在他让我颤栗我就颤栗,压抑个什么劲。
“高铮。”
“嗯?”
“高铮高铮高铮。”
“嗯。嗯。嗯。”声音一次比一次近,他起身又压了上来。
我用手指划过他的肩,沉沦前还勉强可以出口成句,“怎么把自己给免费了呢。”
他的欲望返了回来,可还是耐心陪我说话,“不是收了八十么?”
我的手指顺着他的肩骨划上他纠结的手臂,实在舍不得移开,可我脑子还转得开,“那是你帮我垫的钱。”
“那你就当盘是送你的。”他开始行动。
我还想说为什么非得有一样是免费的,可脱口而出的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呻吟。
他已懂得如何进攻。
进步如此之迅速,他是天生的高手。
床是他的战场。在这里,他不是战士。
他是战神。
七
折腾到临近傍晚。
我套上裙子,对他说,“我回家。”
他也起身穿衣服,“一起吃个饭吧。吃完我送你。”
我想想,没什么不可以,便点点头,却见他恍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忘了给你介绍,我兄弟。”说着把门打开,叫了一声,“飞子,进来。”
我晕,“你……你……你兄弟……一直……在门外?”音落,只见一只半米多高的黑乎乎的生物冲了进来,热情无比地扑到我身上,把窘窘出神中的我扑倒在地。
本能使然我想叫,刚要出口,只听他大哥及时训出一句“飞子放手!”,这家伙又乖乖从我身上下去了。
我打量他:深色杏仁大眼,耸尖的双耳,一脸锐利沉着,自信又冷漠,油黑和驼褐相辅相成的浓密被毛,我情不自禁伸出手去摸摸,呦,这肌肉长的,结实却不过分发达。这狼狗帅,跟他哥有得一拼。
我打量它的同时,这位弟兄也在打量我,可我俩的深情对望没持续多久就被它大哥给搅黄了。高铮扯起它的脖子,教训它,“你小子见着漂亮姑娘冲动了是怎么,下次再这样就罚你一百个俯卧撑!”
我不由得扑哧笑出来,边提鞋边问他,“它还会做俯卧撑啊?能给我示范一个么?”
“飞子,俯卧撑,来一个。”
当真啊?然后我就看见这弟兄后腿撑地不动,前肢竟然弯曲了两下,仰首挺胸的,还真有模有样。这回我真笑开了,我说,“高飞,你真棒!”它叫飞子,它哥姓高,它不叫高飞叫啥?
高铮也笑,“这名儿还真合适。”
我忍不住上去摸摸它淡褐色的胸毛,又长又密,手感真不赖。可我还没摸够呢,高飞就被他哥儿们给赶一边儿去了,“歇着去吧。”它可真听话,二话不说小步踱到一旮旯去了,边走边摇尾巴,得意洋洋的,然后往一布毯上一躺,很大爷的样子。
我看出门道来了,凑上去仰着脖子问高铮,“吃醋了啊?”
他看了我一会儿,我等着他乖乖承认,却觉着他眼里神色越来越不对劲儿。我反应得太慢,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把我给放倒在床上了,然后,非常不客气地,在他的兄弟面前,又把我给办了一次。
两个人重新穿衣服。
我的头很低,脸很红,尽量避开高飞的视线,可这位大爷偏偏看笑话似的用那俩大杏眼直盯着我。
我又转头看它哥,这位的脸更红,不过倒是知道我在看他,自己开了口,“想吃什么?”
“附近都有什么你常吃的?对了一直没问你,这是哪儿?”
“五道口。附近没什么高级的,都是便宜小馆子,你行么?”
“当然行啊。”我又不是餐餐珍味的主儿,“这儿是我老根据地啊,离我原来大学也不远。你跟这儿住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我走去窗口往外眺,“这儿是不是离老张原来那店特近?”可隔着院子什么都望不着,只看得到暗黑墙头外的黯然天色。
“嗯,不远。”他穿好了,指着碟架又对我说,“有你喜欢的么?”
有啊,当然有啊,一堆呢,重点垂涎我找了很久的苏克西和妖精的那张□万花筒。可我没法开口,给钱他是不会要的,这便宜我不能占——我没打算跟人家再有下文。
我犹豫着,倒是他说,“今儿不早了,我先送你回去吧,下回你再挑。”
我想说没下回了,话到了嘴边就是吐不出来。心一横,去跟高飞道别。它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蹭蹭我,我在心里跟它说,虽然你已经欣赏过我的裸体了,可我还是过来郑重跟你就此一别,日后有缘再见吧。
它似乎听得懂,更亲密地过来蹭我脖子,却又被高铮给拉开了。我笑着跟他出了门。
站院子里,他锁门,我打量这平房,不大,但竟然是个独院,简陋中有安宁。我说,“这里挺好的。”
他有点意外,“你喜欢?”
“粗糙经常比精致更打动我。”这话被我说得,怎么这么文绉。
他深深望了我一眼,眼里闪光,亮过天上的星——如果北京的夜空能看得见星星的话。
没走多远,我俩就到了一家新疆馆子。我认识这家,以前常来,叫了大盘鸡和它似蜜。自从中午美术馆碰面那会儿我俩就没吃东西,一下午又都耗了不少体力,都饿得很,愣是抢着吃完了,盘底干干净净,除了啃剩的鸡骨头——不知道的准以为来了俩从旧社会穿越过来的穷孩子。
我掏钱包要结账,他也不抢。我顺手给他八十块钱,他不收,说,“你请客吃了饭,这个就算了。”
我脑筋转了好几圈,“不对啊。吃饭是吃饭,这八十是你给我垫的钱,我得给你。”
“也行。那这顿饭就我请。”说着他把钱还给我,八十块又回我手里了。
“那还是不对啊,我还得给你……那个……的钱。”我意思是初夜。
他好像并没明白我指意,不耐烦地皱眉叹气,“你能不能不跟我算这么清楚?”
“可我们说好了是我买……你卖……”虽然八十真的是极可笑的友情白菜价,可总比白占便宜让我来得舒坦。
这次他听懂了。他不说话了,起身往外走。我只得追了出去。
他走得不快,可步子大,我跟得有点辛苦,跑了上去。他是真不高兴了,我看得出来,可我不想让他不高兴,他今天让我高兴了那么多回,我不能忘恩负义。
我跟上他,我说,“我说错话了。你别不高兴了。”
他不理我,继续走。
我拉住他,他没挣,总算停了下来。可他把脸别到一边,目光投放在街对角,或路灯,或行人,或来往车辆上,总之洞悉一切,除了我。
好,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就自己钻进他眼里,这行了吧。我握着他手腕的手朝自己拉了拉——我可真喜欢他的腕骨——他轻微动了动,顺也不是,拒也不是,没挪地儿。我继续努力,我把他的脸正过来,再向下拉,然后使劲踮着脚,把自己的眼睛和他的对上。成功。
然后我就触高压电了。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对望,也不是距离最近的一次,可这是他不高兴的一次。原来有的人,不高兴的时候,反而电力十足。
我有点晕,扶着他的脸的双手紧了紧,把他拉得更近,主动地亲了上去,生平第一次。
我亲得非常用心,把他从唇齿紧闭,硬是亲成了热烈回应,大举进攻。
我们和好了。手牵着手,在路灯下走。
“你想怎么回去?”他问我。
“坐公车吧。”我想和他多呆会儿,从他这到我家,公车怎么也得一个小时。我还有一个小时。我问他,“平时做些什么?”
“上学,在家做音乐,或者出去打工赚钱。”
“哪所大学?”
“T大。”
“呀,没看出来,”高材生啊,“打什么工?”
“给唱片公司编曲。有时钱不够了也去几个俱乐部打碟。”
“……夜店?”我很难把他和灯红酒绿联系到一起。
“不是普通的那种夜店,是相对专业的。我不喜欢乌烟瘴气的环境,可没钱的时候不得已。”
“我就说么,外边那些夜店里的音乐,那根本就是Disco而已。”
“是,电子舞曲已经被白领文化彻底腐蚀干净了。北京的跳舞圈子其实也就短暂发达过一年,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用照顾舞客的要求,他们还恨不得一晚上跟着你跑三个场子呢。”
“自己打工……交学费?”
“嗯。”他答得干脆。
“父母呢?他们不管你?”我试探性地问。
他咬咬唇,“我指望不上他们。我得靠自己。”
我忽然对他肃然起敬。勤工俭学的同学我不是没有过,可我没想到他也是这样的。回想第一次见到的他,身上有股子天生的神气,原来这源自于他的坚韧,对生活的不屈。
他接着说,“上次你那样气我,可我就是不忍心删除手机里你没输完的号码。你只打了7位数,后4位有9999种可能性。我不是没想过把每个号码都拨一次,可我……恐怕没那么多钱。”他苦笑,“所以,干脆直接去你家。我一连在门口等了三天,也没见着你,没办法,昨天这才去问的门卫。”
的确省钱又有效。所以我们现在得以拖手坐在电车的最后一排。
111这趟线,傍晚乘客很少,几乎人人都坐着,还有好些空位。电车驶得悠缓,途径东官房、地安门内、景山东街等等站,他眼神一直流连在车窗外,若有所思。我不打扰他,就陪他一起看景儿。闷热的七月,我内心宁静。
我们在美术馆下车。我想掏钱给他打车回去,又怕他不要,正犹豫的当口,他说,“我送你到家。”
“别,离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