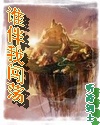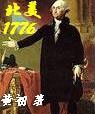闯荡北美-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兴奋状态,便到近在咫尺的南京路上逛逛,吃点儿甜点宵夜后,再慢慢悠悠地踱回家。早上起床后,他可随意地在天井里叫叫嗓子,松动松动筋骨,逗弄一下他养的鸽子。赵君玉曾养了一对无一根杂毛,名叫玉娇娘的鸽子,从头到尾,其白胜雪,名贵至极。当然,他深知自己误场的恶习,是痛煞了剧场管事的头,跑酸了催戏的腿。现如今,住家与舞台只隔了两条马路,紧跑慢跑只需两分钟,他就可以从云南南路二马路的石库门,赶到云南南路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也算是照顾跑腿的了。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他天赋有救护误场的绝技,那就是赶场。只要跟班在他耳朵边儿上一报:赵老板,到点儿了。他人到后台,出不了六分钟,拍粉、点胭脂、贴片子、梳头、登跷、穿行头、保管舒舒齐齐的上场,其速度之快无异于当今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使所有误场的“大亨们”瞠乎其后,望尘莫及。
上海旧时候邀角儿唱戏一演就是一个月,付的是包银,究竟是谁订下的规矩已无从得知。京城里凡南下上海演出的,多大的角儿都认可了。谁要是连唱一个月体力应付不下来,就只能靠吸大烟提精神。没有一个艺人愿意将自己打小吃尽苦头练就的“好玩意儿”,葬送在体力不支上。梨园行的角儿们在舞台上献给观众的每一分钟和他们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演员生活的特殊性,使他们活跃在多姿多彩的舞台上。舞台情绪,特别是舞台激情的释放,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关系到艺术生命。一般常人无法体会中间的奥妙。赵君玉赚了一辈子的大包银,天天满堂身体哪里顶得住。就在他最当红的时候,便好上了这一口。他取大烟提精神、兴奋神经之利,而不顾其带来的大害。在石库门里,专设了一个房间给他抽大烟。想洁身自好戒了烟瘾,已成奢望。他没有退路了!流言腾云驾雾般地从石库门的那个房间,飘出了弄堂里,散在了马路上,与他的艺术生命一齐随风而逝!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了保持“角儿”的体面和自尊,赵君玉退养在云南,让唯一的儿子赵鑫宝成为石库门的第二位主人。赵君玉尝够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楚,没有舍得让独子进梨园行。他把鑫宝送进了洋人的学堂,接受正统的教育。赵鑫宝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读完了书,家里有的是钱,不用他出来做事养家糊口。再说他和他爹一样,长得甚是儒雅清秀。很快地就有媒婆子上门给说了一门亲,是北京的一家世代大地主、天津大买办家的千金,叫佩君。轮到赵鑫宝当家那会儿,正是
抗日战争期间,虽没有了大靠山,他们在上海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把石库门的房子租出去,靠收房租和佩君娘家带过来的钱过日子。先租出二楼西厢房,再是左面的东厢房……
等到了上海解放后,他们住的屋子就仅剩底楼了。政策不允许他们再做二房东收房租,房子都归国有了。没有了进项,就要坐吃山空。但是社会稳定了,京剧演员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赵鑫宝在梨园行凭赵君玉这三个字还是有号召力的。于是,自己组成了个民间京剧艺术团,并狠了狠心,让唯一亲生的、十三岁的女儿开始学旦角儿戏了。
按梨园行的要求,六七岁学戏是最佳年龄。他们常挂嘴边儿的话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等十六七岁学成后,正好挑大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但是十三岁学戏,已属太晚,很少能成大器的。可是赵鑫宝偏不信邪,按戏班儿里的话说,他“蛮”上了。他就不信祖师爷不赏他女儿这碗儿饭吃。在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不像“棒槌”(傻瓜笨蛋的意思),具备学花旦的所有条件:她脸庞秀丽,嗓音甜美,身段娇小玲珑,这典型的赵家门里人的素质,仗着遗传基因到了她身上。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学唱戏。经过五年的刻苦勤奋,十八岁的女儿,争气地挑大梁挂了头牌,跟着爹跑码头赚大钱了。她扮起戏来与爷爷赵君玉像极了;要是她爷爷还健在,能得着点儿他的真传,又或者她再早一点儿学戏,没准儿还真成了赵君玉第二,红遍江南。
由于父女俩长期在外面,上海就留守了佩君及她母亲坐阵看房子。而人民政府开始实行户籍制度,不在本地长住的居民,将不保留空余的房间。赵鑫宝哪里懂得这一套,他只知道,他在石库门里生,就永远是石库门里的主人。等他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石库门就只剩下底楼的三开间东厢房,其余的房间都被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让外来户住了进去。所幸他们凭着出生证,报进了上海的户口,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儿了。也是在那时,一阵公私合营的风,吹到了赵鑫宝的私营剧团,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他也不能例外,父女俩把私营剧团“国营”化了,就在他们当时安营扎寨的地方——湖州。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再怎么宝贝自己的女儿也得把她嫁出去,赵鑫宝不得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他想起新近团里正好来了个从江苏省戏校毕业的文武小生,小伙子看上去老实忠厚,说不定和女儿能结百年之好。上海人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可这次不同,这次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待字闺中的女儿满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由赵鑫宝做主把女儿嫁出阁了。
婚后,小两口子在台下出双入对,在台上也多半恩恩爱爱夫妻相称。第二年的3月,他们便有了爱的结晶,一个在石库门里出生的女孩儿,那个在睡梦里寻魂的灵——小玲。我的降临给石库门的家带来了生气,给姥爷赵鑫宝和姥姥佩君带来了无比的喜悦,给爸妈带来了欢乐。正月里梅花盛开,我的名字里有了梅字,为了纪念赵君玉,便把玉字放在了梅的前边儿,玉梅则成了我的学名。
妈妈在石库门的家喂养了我八个月,舍不得扔下我走,没有办法,姥姥答应陪她去照顾我。八个月大的我,随妈妈来到剧团,全团“208将”逐一把我抱了个遍(他们团里有二百零八个演员,声称梁山好汉208将)。两年里,我被姥姥从石库门的家抱到剧团,再从剧团又抱回石库门。有一回,大概这样的往返间隔稍稍久了一点,妈妈想我想得厉害,她又跑不开,便托剧团的同事给姥姥捎信。姥姥又抱我去剧团了,当妈妈兴高采烈地从姥姥手中将我接过去的时候,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哭得天摇地动。妈妈没辙了,照准我的屁股“啪啪”两下子,我立刻停止了哭声,乖乖地让妈抱在怀里。姥姥不高兴了,责怪妈妈把我吓着了。不过,打那以后姥姥抱我往剧团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而我也已到了记事和认人的阶段。我喜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等历史文学,这大概与我在娘胎里,以及打小在后台耳濡目染戏台上的历史人物分不开吧。
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弟弟。妈妈也在石库门的家里喂养了他八个月。等妈妈再回剧团时,又开始高喊减薪了。妈之前已经从550元减到了250元。那年,不但要减薪,而且还展开了批“三名”、“三高”的运动,来势汹汹。爷爷从北京、上海的同行那里听见了许多名“角儿”遭排挤受迫害的消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剧团里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带着爸妈从湖州回到了上海石库门的家。我们全家团圆了,也全体失业了。九口之家(姥爷让妈妈学戏时,领养了被人遗弃的一儿一女),靠了变卖古董、细软、整堂整堂的红木家具后,又靠姥爷投资的西施公司(香港的分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维持了三年坐吃山空的日子。
1966年春,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上海也紧跟在后。我们石库门的家已然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除了几套爸妈唱戏的行头和一副水钻头面没舍得卖,被藏了起来。家已然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正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故事。全家的大人这时哪边儿都靠不上,既不在内行揪斗的圈儿里,也没缘“份”卷进外行的政治漩涡中,他们归街道里弄派出所管。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和戏曲也沾点儿边。石库门所属的黄浦区街道里弄那帮婆婆妈妈的干部,上门动员姥爷姥姥和爸妈要响应号召,发挥会唱戏的特长,争取做革命人。为了紧跟形势,姥爷带领我们一家排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演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这出戏里,爸爸演李玉和,妈妈演李铁梅,姥姥演李奶奶,姥爷扮演鸠山,舅舅演日本宪兵队长,姨演隔壁邻居大妈的女儿,而那个卖烟卷儿的小女孩就是我演的。除了叛徒王连举和几个群众演员外,我们全家上阵,将整出的《红灯记》搬上了舞台,一时在黄浦区传为佳话。同时,我们一家在九江路上又出了名。因为普及革命样板戏,使失业的大人都有了工作。石库门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避风港。没法避免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牵连的是姨和舅,先是姨去了新疆军管的建设兵团,然后是舅舅随了六九届一片红——即“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场插队落户了。
姥爷被安排进了一所小学,他像管理剧团那样管理着全校的一切勤杂事务,兢兢业业。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一下课,就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玩儿,这多半是我们的零用钱花完了。姥爷在带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忘到九江路和云南南路十字路口的南货店,给我们买零食吃。他总是多买一份儿放在身上,开始我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酷爱孩子的姥爷,凡石库门里的小孩,不管长得多丑,多调皮,多惹事生非,多乖,多听话,多可爱,他都一视同仁,都喜欢,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摸出零食给他们吃。孩子们见了他,都亲热地管他叫爷爷。就在全家失业那会儿,以前剧团里的同事们经常的从全国各地来上海,都喜欢在我们石库门的家落落脚,他们前脚进,姥爷就夹起值钱的后脚出,用当了东西的钱照顾客人的吃喝。有的人会说姥爷是败家子,但我不这样看,我特别欣赏姥爷身上的侠气和仗义,就算散尽了家财,也比没有人情味儿的守财奴要强。姥爷虽然在戏曲不算是真正的内行,可对行里的事儿是很清楚的。他借着酒精的力量,对江青控制文艺界迫害艺人的行径,拍桌子、瞪眼睛地骂骂咧咧,姥姥劝都劝不住,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我不怕。”姥爷晚年总是借酒消愁,逐渐地养成了习惯,喝了点儿酒后,就从后门的弄堂踱到南京路,再拐弯沿着云南南路绕回到九江路石库门的家。他郁闷,他烦心,女儿女婿学了唱戏这行,却没了用武之地;小儿小女又离家那么远,让他日夜地揪心;他认为家是败在了他手里,无法使我们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郁抑成疾,得了心脏病而不自知。我当时太小,不知怎样地宽慰姥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为姥爷跑腿。听见姥爷叫一声:小玲,替姥爷去买包“大前门”;或者半斤黄酒;又或者二两高粱。我会乐得一跳一跳地沿着九江路的上街沿,直奔小烟纸店和酒店而去。当我懂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含义时已经太迟,姥爷早已离我们而去。
姥爷毕竟受过西洋教育,当爸爸在建工局底下的基础公司做了一名临时工,妈妈也上班后,他让爸妈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了。爸爸会唱京剧,在建工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从而被转为正式工,分派在采购科成了一名科室干部。爸爸的家史,我大部分也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爸爸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六岁那年,石库门的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又浓且密,无论是他的体态,还是他的笑容,都像极了贴在每家每户墙上的那个人——林彪。爸妈管我叫他爷爷,我心想,我已经有一个爷爷了(我平时管姥爷就称为爷爷),怎么又出来个爷爷呢?而且,大人们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人说他像画上的人。这个爷爷特别喜欢弟弟,见了他又亲又抱的。两个爷爷在一块儿吃酒聊天儿,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晚,我和弟弟都上床睡了,他们还酒兴正酣。不过,这个爷爷只在石库门里住了几天就不见了。我整十岁时,爸妈替我过大生日,这个爷爷又来了石库门,拉着我的手看了个够,他和上次一样,住了几天又走了。于是,我缠上了姥姥问这问那的没完没了,姥姥被我缠得没办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个爷爷的故事,并告诫我不得外传。原来,我这个爷爷是爸爸的父亲,从他这一代往上是世代的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