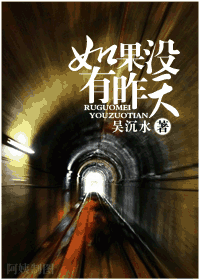����-��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ҿ��һ����������
��
����һ����Ѫ���������ϡ�������
��
������������������Ϊˮ��������
��
�����������֣������Ĩɱ��ȥ��������
��
���������Ұ�����˹��������������������ˡ�������
��
����Ϊʲô��Ҫ���ġ�������
��
������Ȼ������ȥ������Ҳ�����ɡ�������
��
������Ȼ�����Ҹ���Ҳ�������ٻ������������գ��ٲ����Щ���ף������������ļ��ȡ�������
��
�����㰮�ң���ϧ�㲻���ң��㲻�Ź��ҡ�������
��
����Ҳ�Ͳ��Ź��Լ���������
��
�����Һγ������㣬��ϧ���Ѳ����š�������
��
�����ҷŲ����㣬Ҳ�Ų����Լ���������
��
����û���ᣬ��ֻ����Ѫ��������
��
���������뽫���ϣ��������о���ʧ�룬һ�統���ҳ����������ڳ���������Ϸ��������
��
�������뽫����˵�Ķԡ�����������������������������������Ϊˮ����˵�Ķԡ���������
��
���������ܺ�һ�룬���ѳ�����ȥ��������
��
����������������������
��
�����뽫�����ѽ�ƣ������������
��
�����㲻��ô��������
����
����������
�����죨�£�����Ū��������������������
������
���������Ҵ����粣����ˤ���˾�ճ�����������˽��������ֽ��ҵ������һ٣���
�����������飻���Ǻ�����˽�ֺ�����̣���������IJ������ף���
���ִ����Ϊ������صļ������ȵ���һ�죻����̥���ǣ����Լ�ĥ�ðٶ����֣���
������һ���Ӷ����������������ط��ʱ�̣��Ǹ�ʱ���˽����������°����ҡ�����������������
��
��������������������������������������������
����
��ʮ����
������������������
���������������㰮���𣿡�����������Ϥ�ĵͳ���������
��
�����һ�ͷ�����������У����뽫�������Ц��Ӣͦ��ü����������ᣬ�������顣�ҳճյ�˵�������������Ұ������������Ұ��뽫������ӹ���ɡ���
��
����������������������������Ȼ�����Ц������һ������
��
�������Ȼ�������������⾡�š��ڰ��������������������
��
������Ȼ�����۾����Ѿ��ų�һ���亹�����ڷ��У����ڴ��ϡ���
��
�������ܺð������ټҵĴ����⣬��Ȼ��������С���������������һ��ج�Ρ�������
��
����������תͷ���뽫���������ߣ����������۾���˯�����𡣲���ج�Ρ���
��
������������̾��������ʵ�ģ�����ج�Ρ�������һ������������һ�ж����Σ��ö�ã�������
��
�����Ҳ�˵�������������뽫��һ�ƺڷ������۾�������ס�˶��ϵ��˺ۡ���ͦ�ı������Ǹ�����ʱ�ĺڿ��۾��粻֪ȥ�������������������ǰ���ƺ���ʱ��ȷ���һ��������ߡ�������
��
��������˾��������黳�����Ծ����֣����������������Ĵ���������������������Ω�������������Ĺ۲�һ�£��ŷ���������Ĵ��Ρ���һ�ν��ǣ������¡����ϣ��������������ֱ̿��������ң�Ц���������������������
��
�������뽫�����������������ỽ�����������ѡ�������ôҲ���������ᣬ�˿̾�Ȼ����Ԥ�ع�����������æ���ֽ�ס��Ⱦʪ���ġ�������Ϊ�������ֻ�������ǰ���֣���ʱ����ָ��ץ��������Ļ���ͳ����㲻֪��ô����������������û�з�����˯�ݣ����ǶԸ�����õ��������������ĵ��ˣ���ʵ�����Լ�����
��
�����ұ��ͷȥ��ȴ��Ȼ����ץסҪ���ص����ơ�������Ȼ��ͷ�������뽫��ڵ��۾�����
��
���������࣬������ʪ������ġ����������㵽��Ϊ�����ᡣ���������ʣ��������㵽���ǰ��ҵģ����𣿡�������
��
�������ԣ����ԣ������Է��������������ҵ�������
��
�������ʣ��������������Һð��㣬�Ҹ���ô�죿����
��
�������ַ��������������������������������ߣ��뽫��������ң�����Ҳ�����л��ᡣ���������Ļ��������һ��ٰ��㡣����
��
�������������˲����������˲����ȥ�������У������������������������
��
��������Ȼ���ٷ�����ȥ�������������¡���������������������ǰ���ҳ����ǵã���Щ���õ����ӣ����������졣����
��
������������ס���䡣��Ҫ��Ҫ�����㲻Ҫ�������졣���Ѿ������ɾ������㲻Ҫ�������죬�뽫��������
��
�����뽫˵�������������������������ʲô�����Ը��㡣���㰮�ң�����������˵����˰�Թ��������
��
�������ĵ����������������������������������
��
����������������������������ã��������������һ�������������������°��㡣����
��
��������˵�����������ڴ�����ֱ����������������ҡ���
��
������˵��������ħ��������һ��ħ������ֻҪ�Ҷ�������һ�����⣬�Ҿͳ����Ļ����ٲ������¡��������������ʲô��������ù��ҡ�ֻҪһ���𰸡�����˵һ�䣺�뽫���㣬�������⣬�������ġ��ұ��������أ�������֩�����������㻳�С���
��
�����뽫��Ц�������������������ϲ���ħ��������
��
������˵���������ԣ������Ҳ����㡣����������Ƭ�̡�������
��
�����뽫��ȻЦ��������§�뻳�������ҵ�ͷ����Ȱ���������������������ˣ�˯�ɡ�����
��
�������ã���˯�������������뽫����˵���������뽫������һ�¡�����
��
��������˵�������뿪�ң����������Խ��ܡ�����
��
�������������Ī���������У��Һ������ۣ�ֻ��һ���þ�����������
��
�����뽫��Ȼһ���������������������������ʱ��˵�����������ġ�������ԭ����Ҳ�����ģ����ǿ�ϲ�ɺء���
��
�����ұ����۾��������У������뽫����������������������ҡ�������ĪҪ���ҡ�������˰��㡭��������������
����
����
��ʮ����
����������������
�������峿����������ȴ�������۾���������
��
�������������Ժ���������������ǰ�м���æµ��Ӱ�ӡ�������
��
����ȫ��һ������Ҳû�С�������
��
������ɤ�Ӹ�����ˮ���߾�ȫ����ֻ�ܶ����촽��˵����һ���֡�������
��
����Ϊʲô��������
��
����Ī���뽫�ֶ�������ʲô������˯���С�������
��
�����������Ѿ����Ҷ��ƣ������Ҳ���˵�������ĵĻ�����������
��
������־��������˺ܳ���ʱ�䡣������
��
������ͷѹ��һ�������ij����Ķ������Ҳ��DZ��档������
��
�����ۼ��һ��о�һ���Ĵ�ʹ����о�������Ϥ������ע�䡣������
��
����ֻ�����Լ�����ʵ���õ�С�������ڴ��ϣ����ܶ��������˰ڲ���������
��
��������������������
��
�����������뽫С�������Ļ��ҡ�������
��
�����������ҵ������ִչ������������ҵ�����ĥ�伸�£�ƫͷ������һ��˵�����������Ǻ��̡���������
��
���������ߵ���˵����������������һ��Ҫ��Ժ����������²��ס�������ԭ�����ټҵ�˽��ҽ����������
��
�����Ҳ����𣿡�����
��
����û�С��ҿ�����������˵���������붫����������
��
����ֻ�������е㲻֪��·�����������ۡ�˵���������������۾���������
��
�����뽫����������������벻���ĺ��£����������������ݴ������������Ժ����ô����ô���أ����������ƺ��ڷֱ��˵����������ʲôҲû�������������չ˵úúõģ�Ϊʲô�����Ȼ������������������
��
����ҽ��Ϊ�ѵؽ��ͣ�������������������������������
��
�����뽫������Ļ������е��ʣ���������˵������Ͳ��ף�����ʲô��˼���ѵ������������������ҵ��ֺ�Ȼ����ץ�ý�����������
��
����������ģ�����ģ���������
��
�����뽫������Խ��ԽԶ��Ʈ�ø߸ߡ�������
��
���������������ˡ�����������������
��
���������ܹ������۾���ʱ�����������ۻ����İס�������
��
������ããһƬ�ĵط������˲��������������������
��
������һ���������������ߵ��ˡ�������
��
�����������������ˣ���������
��
�����뽫�������������þ�ϲ���������ݡ�������
��
���������������ҵ��֣����Һ�Ȼ����һ�ᣬ�غ����ա�������
��
��������ǿ�����촽���������Ҳ��ˣ���������
��
���������ŵص�ͷ�������ң��ֿ��ĵ�Ц��������������
��
��������������������
��
����������������۾���������
��
����Ϊ�β���һ�����𣬴Ӵ�����������������
��
������������ˣ�������ǰ�ˣ��������ⶼ������ֻ��˵�����ķ������顣������
��
������ʲô������������
��
�����뽫����������������ƶѪ�����ա����������������������������ġ���������������
��
��������������
��
������ô���������Ķ������ˣ��ټҵ�ҽ��������ҽô��������
��
�����ѵ�����������ҽѧ��ˣ�������
��
����������š�������
��
�������������������뽫���Ϸ����������ҵ������ʣ��������㵽���ڷ���ʲô�����㣬��ô�ෳ�գ����Լ����嶼Ū���ˡ���������
��
���������ȻƮ�ú�Զ��������
��
����ʲôʱ����Ҳ�����ʹ��ң��㵽���ڷ���ʲô��������
��
������ʱ����Ϊ�������õ����ϣ��龫���ǣ���˼ڤ�룬��ҹ������������
��
������˵���������뽫���ҵķ��գ��������ҵġ����ֺαعܡ���������
��
�������������ã����ͷȥ������̾����������
��
������˵���������뽫�����֪������������ʲô����������
��
���������ȵػ�ͷ�����ҽҿ��յס�������
��
������������ÿһ�仰��ÿһ��������ÿһ�����顣������������ʵ����������������ҿ�������ʲôʱ���棬ʲôʱ��١���������
��
�������������ҡ���������������
��
����������������������ԣ���ֻ�ܰ����һ�ж����ɼٵġ��뽫������������ݡ���������
��
�������ִ�������������������Ц����������ˣ�����Ҳ����������ǰ���������ģ������̾��̾��û�������Ҫ����������
��
�������������ң�����Ҫ����§�ڻ��������
��
�����������ҵļ磬���ұ�����۹��Ȼ������ɲʱȫ��һ����������
��
��������æվ���������������������������飬��æ�ٿ���һ�ۣ��ɿ�����ſ��߳���������
��
������ֱ����Ҳ�Ƶij�ȥ�ˡ�������
��
������Ҳ����Ϸ�������Լ���������
��
�����ǵģ��϶��ǵġ��Ҵ��Լ���������
��
�����컯Ū�ˡ�������
��
������ô����ϣ���������ϣ���ʹȫ�ޣ��������������ҽԺ�С�������
��
������ֻ�������������˽ᣬ˭֪������һ�ձ�һ�պ�������������
��
�����뽫����û������������
��
������������ʱ����ʹ�ķ���������Զ������һ�棬����������Զ���ںڰ��Ľ�������ȫ���ǡ�������
��
������������ʱ���ֿ�ʼ����������������
��
������Ȼ������������ֻ�ǡ����������������ҿ������ĵط����ҵ����ұ����ķ����ɡ�������
��
���������ˣ�ԭ�����ľ��ء��������뽫���Ӷ��ɵ�������������
��
�������ڲ��ɲ�����Խ��Խ�£���Ȼ�����������š�������
��
������֪����˭��������
��
����������뽫�������������ţ�ֱ��ֱ��������ʾ���ǵġ���ϵ����������
��
��������������ˣ��������ܺ�һ�ɽ������أ�˭������ô�����������ҵ��ţ�������
��
������һ�߲£�һ��˵����������������������
��
�����ѵõ���ʹ�����벻����������Ȩ�������ÿ�Ц��������
��
��������һ��СС��Ȩ���������ڵ��ң�Ҳ�ǿɹ�ġ�������
��
�������Ŵ�������
��
�������۾�һ������������Ȼ���㣿�����������������
��
�����ҶԴ��˲�����Ϥ�������ڿ���������Ȼ�������еĸо���������
��
������Ϊ�����ˣ���Ϊ�������������������ɣ�������Զ�����������뽫���Ͽ�������ϡ�������
��
��������ͤЦ������������ô���������㣬���Dz�����˼����������
��
��������ô֪���Ҳ��ˣ����������ھ��ʣ��ƺ��е㲻����ò����������Ҫ���⣬������뽫֪ͨ����ô����һ���������壬��ȻҪ����ʮ���ֵľ���Ӧ�ԡ�������
��
���������ܺ�Ҳ�г�ı���ߵ����ɡ��Ͼ�������ͤ����Ƭ���ܺ����С�������
��
��������ͤ�����֣���������ԭ��Ҳ��֪��������һ������������Ȼ����������֣�������ס����Ҳ��֪���ɣ�����������ҽԺ������ҽ�����������Զ���ӧΪ�㿴���������ҽ�����Ҵ����������Ժ���Ȩ���������ڣ���Ȼ����Ҫ���ϰٱ�����������
��
������˵��������ԭ����ˡ���������
��
����������ֻ�ܷ������ݾ���Ӣ�۵Ľ�ɫ������СС��̽���ߡ���������̯��˫�֣��ʼ�������������Ǵ�æ������������Ҳû�У����������ɣ���������
��
��������Ҫ���ҿ������С�����ҵ��ǻ������ġ���������
��
��������̸Ц������֪��ʶ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