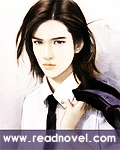并非阳光-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笃定,真的,从心到口,都那样笃定,无一丝怀疑,却手脚还是冰冻,一阵一阵,抖得压都压不住。
于是我又惊恐的发现沙发。
那么大的一组沙发,从第一次进这里我就见过,众人坐在上面开会,林信也坐在其中,就在我眼前,我竟恍如未见,察觉不出任何意思。
但我仍记得那短短对白。
我对安燃说,「书房至少应该有张沙发,自己坐着,其它人都站着说话,多不可一世。」
安燃说,「抱怨什么,你好好读书,等将来有自己的书房,大可以尽情摆设,放多少沙发都可以。」
我惊惶一阵,随即粗暴打断这无聊思绪。
办公室有沙发是常事,哪有什么暗示?何况我们说的是书房,又非办公室,两者怎么相同?
好了,安燃,好了。
你目的已经达到。
我一早就已经投降,举双手,跪双膝,如果你要求何君悦再磕个响头,绝对可以得偿所愿。
若你还有不甘,最多也只是我资质不够,懂得的投降招数太少,不能满足你的胜利欲。
何必如此?
夜深了,华灯亮起,我被装载在最璀璨的顶端。
俯视,喧闹赌场一目了然,隔那么远,仍那么吵,种种输赢刺激如激光线横冲直撞,尽打在办公室冰冷玻璃另一面。
我无法再安静地坐,那会把我逼疯了。
勉强自己站起来,扮作坚强从容,在落地玻璃前装作高高在上,俯视众生。
身影露出来,也许招来好些人在下面仰头看。
我不在意。
这样站着,露一个挺拔颀长的身形,引得众人目光,不过是因为安燃必定也曾经这样做过。
这想法令我可以获得片刻安宁。
片刻就够。
有这么一点空隙,足以让我想起太多诺言,然后用这些诺言,把扑过来的绝望狠狠丢弃。
安燃不会离开,他怎可能?
记得他多么狠吗?他用烙铁在我身上留下一个安字,还说,「君悦,你不能不要我。」
他说:「我是你的,只能是你的。你必须要。」
他问我,「若你我没有百年,残缺不堪的安燃又何必活着?怎么活得下去?」
他说过这么多,我一点也不想听的诺言,怎么能抛下一句我不想活,就消失不见?
不是百年吗?
这才多少天?
安燃总说无可奈何,其实我才是无可奈何那个。
他总能玩他要玩的游戏,总能让我伤心欲绝。
可是今个太过分,伤到了我的魂魄。明明知道他不过是诡计,我还是心碎,心碎,碎到无可再碎。
碎都已经碎了,竟还不知道该怎么投降。
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站在璀灿灿水晶灯下,真的无可奈何。
「安燃,我服。」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重走投降的旧路,「我认输,你出来吧。你无所不能,我不可救药,我认错。我知道自己不可原谅,我知道什么都是我错,我错了!错了!错了!求你,大人有大量,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脆弱的宣言了无新意,来来回回不过那几句,天知道我字字血泪,真心都碾碎在里面。
「就算你要我上吊,至少也给根绳子。」
我啜泣,在这高处呜呜咽咽,悲愤莫名,继而哀哀切切地求,「安燃,我真活不下去了,你出来吧,只当最后一面。」
到这般田地,依然毫无响应。
我都麻木了。
什么自杀对不起过去的安燃?什么安燃珍惜的身体,不要损伤?
从头到尾,只有我傻。
我认真的想,痴痴的,但很决绝,仿佛片刻就想好了。
能这么清楚的想事情,真的很让我自己也吃惊。
我想得很笃定,和笃定安燃躲在暗处一样,离开落地玻璃窗,转身坐回书桌。
不一会我就找到了一件宝贝,它那么闪亮,就横着摆在桌上,好像天赐给何君悦的一样。我拿起来,看着这裁纸刀,又新又漂亮,灵气都在薄薄的锋刃上。
本来在哭的,这刻我忽然又绽开了笑。
如林信对我所言,「君悦,你可以不信。」
我借着套用一句,赠给安燃。
安燃,你可以不出现。
真的。
你可以。
拿起裁纸刀的那瞬间,我听见门把扭动的声音。
这是世上最有冲击力的声音,那么轻轻的,滴答。本来我要摧毁我的生命,不过一瞬,那要摧毁生命的毅然,反而被摧毁了。
「安燃!」
我丢下裁纸刀,它不再是天赐的。安燃,才是天赐我的。
「安燃!安燃!」我扑向我的安燃,虽然他那么狠辣,却不由得我不抱紧,失而复得是最恐怖的教训,我连哭都不敢,十指紧扣,抱着喃喃,「安燃,都是我错,都是我错,你不要走。」
我颠来倒去,呜咽着赌咒发誓。
拿我这一生,拿我的命,发誓何君悦再不敢招惹安燃。
他说东我不敢往西,他说月亮是方的,那就是方的,他说我错,那我就有错。
再没什么真理,什么是非曲直。
我说了这么多,舍弃这么多,却听见林信的声音。
林信说,「君悦,你冷静一点。」
他的话真有效果,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抱错了人,赌咒发誓搞错物件。
何止冷静,我完全冷了。
我直勾勾看着林信。
材信还在说,「君悦,你要冷静。」
他说,「抹干眼泪,站起来。」
这个时候,他居然来励志。
我真无助。
我恳求地看着他,「林信,你告诉我,安燃到底在哪?他不可能走的,怎可能?」
林信叹气,又把刚才说话重复一次,只是更有力道,「君悦,冷静,抹干眼泪,站起来。」
他指着落地玻璃那头,对我说,「宁舒来了,你要出面。」
我魂魄早失了大半,怔怔问,「为什么我要出面?」
林信说,「你是我们老大。」
我摇头,「我不是。」
林信坚持,「你是。安老大指定的。」
他不该提起安燃。
一提,我失去的被撕碎的魂魄又回来了。
「我不是什么老大。」我不断摇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晃着头,颤抖如一棵断了根的小树。林信忽然狠狠握住我的肩膀,制止我。
「冷静,君悦,冷静一点。」林信深深看入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这不是我们当年的游戏,这是真刀真枪的现实,做错任何一件事,都改不回来。明白吗?」
他的口气出奇的充满震慑力。
我被震住了,呆呆看着他。
林信说,「安老大已经通知各道,你是他接班人。君悦,宁舒就在楼下,你必须挺起胸膛去见。这是你第一次正式和对手打照面,输了这局,很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我反问,「万劫不复,那又如何?」
我不在乎,才不在乎。
让安燃去处理,让安燃去面对。他下个通知,指定个什么接班人,就以为可以挥挥手只留个潇洒背影?
做梦!
第二章
林信被我惹火了。
我们毕竟认识那么些日子,他又离我这么近。他有没有愤怒,我当然清楚不过。
他眼底腾起怒火,前所未有的凶恶,认识他那么久,我从不知林信也有这样凶恶的一面,连半失神中的我都有些吃惊。
那样怒不可遏,几乎以为他会对我动手,但想不到怒火烧了刹那,又骤然全冷下去,沉淀在眼底,只有黯淡的痛心。
林信再度开口,声音居然比刚才还温柔。
握着我双肩,怜惜地问我,「君悦,到现在,你还以为安老大是在和你玩吗?」
他说,「君悦,你要明白,没有永远的下一次。」
他说的话,我听得清楚。
怎么可以这般清楚?这样撕碎我命的话,还说得这样温柔怜惜。
我想蜷成一团,把自己蜷成一个再不用面对悲伤的茧。
但林信不许。
他紧紧抓住我,逼着我,对我说,「君悦,安老大杀出一条血路,坐上这位置,护着你到如今。但现在开始,你只能靠自己。」
他说,「去见宁舒,你必须站起来,坐稳这把交椅。」
我还是摇头。
我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越走越是绝路,进退都找不到丁点生机?
我不要去见宁舒,我什么都不会,见了也是败仗。林信真不是东西,我已经伤透了,遍体鳞伤,他却还要逼我上另一个战场,算什么朋友?
我拒绝,「这把交椅,我不坐,你想坐,你就坐。」
林信差点咬碎牙,「我就算坐上去,够本事护得住你吗?」
我也咬牙,「我又没得罪哪个,怎么就这么被人容不下了?要你们分分秒秒的来护?大不了当我没认识过你们,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耳边风声骤起。
眼一花,林信拳头已经到了我面前。
不知为什么,又硬生生停住,无法再往前伸出一分一毫。
「君悦,君悦,你怎么天真得那样可怜?」林信松了拳,筋疲力尽,颓然苦笑,「你姓何。你知道自己身上都流着谁的血?你又知道自己外公父兄留下多少血债,结下多少仇家?」
林信悲叹,「你现在是何家唯一根苗,昔日风光无限,呼前拥后,一旦真的无权无势,无依无靠,谁肯放过你?这世上到处都是落井下石之辈,别说何家仇人,就算你撞到素来没多少恩怨的人手里,冲着你这家世,可以尽情作贱你一番,也是个炫耀的资本。」
他问,「君悦,没有权势,这世上还有哪个地方容得下你?」
他问,「君悦,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安老大辛苦逃出一条命,不隐姓埋名过他的日子,却还要拼死打这个江山,占这把交椅?」
他问,「你又有没有想过,安老大为了坐这把交椅,欠了多少血债?结了多少仇家?请你想一想,君悦,你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什么,但到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不想。」
林信说,「如今他把所有争来的都给了你,你败了,就是他败了。你得罪人少,或者还可以求个痛快,他呢?你知道他手段有多狠,把多少人得罪到死地?你想想他失去这个江山,会有什么下场?」
林信最后说,「君悦,别这么自私,永远要别人护着你,为你去挡刀枪。你自私了一辈子,今天,至少站起来一次,护着别人一次。宁舒正在等你,如果你真有那么一点爱过安燃,你必须站起来。」
我失声痛哭。
好痛。
一边痛哭,一边咬着牙,仰头嘶哑地吼,「纸巾,给我纸巾!」
好痛,真的好痛。
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剩。
但还是要抹干眼泪,还是要站起来。
止不住眼泪,却还是必须挺起胸膛,面对宁舒,上这个战场。
从地毯上站起来时,双膝都在打颤。
林信扶住我,我坚决推开。
膝盖打颤我就撑着墙。
跌倒了,我就再站起来。
「林信,」我找不到自己的呼吸,却总算还口齿清晰。电子书,说,「找套衣服来,我要换。」
我要见的是宁舒,安燃的敌人,不可以输了气势。
但,就算不够气势,我也必须去见。
没什么可恐惧的。
我已经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剩。
一点一滴,自己还未曾明白,就已经败个精光。
但只要未到结局,就必须挺起胸膛,站着。
多无力都要站起来,心可以碎,脊梁却必须挺直。
不为什么。
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
但我真的真的,曾经那么,那么,那么,深爱过安燃。
不是那么一丁点。
深深的。
深深的,爱过。
爱着。
不知哪里借来的力气,至少我终于站了起来。
双脚踏地,有了支撑,腰杆就可以挺直。
那深藏不露的阿旗自从滚出去后,一直不曾远离,我等着换的干净又合身的西装,最后竟还是他找来的。
我控制着颤抖的手脚,自己入内换了全套衣服,从里面走出来。
卖相应该还不错,穿着笔挺西装,也算焕然一新,只是脸色太差,尤其一双眼睛,谁都看出哭过。
阿旗问,「怎么办?」
他问的是林信,不过我已经想到了,对林信说,「拿一瓶酒来,度数高点的。」
烈酒拿过来,我拔开瓶盖,仰喉一口气灌了小半瓶。
辛辣香醇,够滋味。
好久没试过这样狂饮,如今一开戒,才发现昔口狂气仍留着几分。
打算再来一口,整瓶对付掉的。林信和阿旗一起出手,把酒瓶夺了下来。
林信说,「君悦,够了。」
我体会着从食道到空空胃里滚动的火流,了然。
对,今非昔比,再没有任性的机会了。
等酒气上冲,红了整张脸,把哭过的痕迹掩了大半,就出发,去打仗。
阿旗开道,林信护卫中军,一干保镖殿后。
从电梯出来,前呼后拥,众人自动分开一条通道,沿路都能听见各种尊称。
「君悦少爷。」
「何二少。」
「总经理。」
「老大。」
「……」
半醉半醒间,我在前后簇拥中,举步前行,旁若无人,心里只想一件事,别低头,君悦,昂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