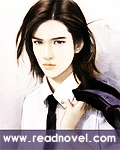并非阳光-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信却说,「君悦,听我说,公司需要你。」
我冷笑,「公司从来没有需要过我。」
林信严肃起来,「你如果不回来,怎么保护安燃?」
我说,「安燃什么时候需要过我的保护?」
从前竟会听林信胡说八道,真可笑。我不知道自己会这么蠢,安燃,安燃是什么角色?他需要我保护?他只需要一个供他用不同方法逗着玩弄的何君悦。
「现在。」
「什么?」
「君悦,」林信说,「你必须回去。」
他说,「公司出事了,需要老大回去处理。」
我盯着他。
林信的表情很认真「这事关乎安燃生死。」
我心脏猛地一顿。
他说,「君悦,你可以一时怒气,真的不理会。但我不希望你日后为此后悔。」
他问,「你怕不怕安燃没命?」
我说,「你骗人。」
林信一字一顿,「我不拿这种事玩。」
林信说,「君悦,我不是你。」
这人真绝,此时还不忘拿剑狠狠刺我一下。
更绝的,是我。
被他刺了,还要听他的话。别无他法。
林信问,你怕不怕安燃没命?
我当然怕。
听他这一问,我心都颤了,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又被逼上梁山。
我和林信一起回公司,阿旗当然也少不了跟来。
三人同车,还在路上,我就忍不住了,问林信,「到底什么事?」半信半疑,又惊又惧。
林信把司机和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沉吟。
他问我,「方标,你记得这个人吗?」
我茫然。
阿旗解围,提醒道,「君悦少爷,开会的时候见过的,他眼角上有道疤痕,大家叫他狼眼标。」
我这才隐约有点印象,点头,问,「怎么?他和安燃有什么关系?」
林信说,「阿标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不够冷静。前几日为了一点口角之争,火气上来,对一个泊车小弟动了手。那家伙被阿标踢断了两条肋骨,没想到跌倒时碎肋骨插入脏器,送到医院已经救不回来了。」
我明白过来。
这般斗殴,在黑道原来就是家常便饭。不过出了人命,处理起来难免多点花费。
我问,「对方家里还有什么人?要赔多少?」
林信说,「钱不是问题。但那人是宁舒下面的小弟,平常干点跑腿的杂事。」
我皱眉。
牵扯到宁舒,问题就有点不妙了。
我问,「宁舒拿这个向我们找碴?」
林信看我一眼,说,「昨晚你也在场。他在我们面前玩得如此尽兴,这件事却一个字也没提。」
这当然不是好消息,只看林信的脸色,就知道宁舒这不提,比提更难应付。
阿旗可能在林信见我前就已经和林信沟通过,在一旁说,「警方今天早上破门而入,抓走了阿标。」
林信说,「杀人罪名成立的话,阿标这辈子都要吃牢房了。」
我问,「警察查得如何?有证据吗?」
「问题就在这里。」林信沉着脸,「警察还找到了证人,事发时,刚好经过后巷,还看到阿标的脸。」
车内沉默下来。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案子,有关键证人,是很要命的。
我想了一下,冷冷说,「种瓜得瓜,杀人偿命,他做了这事,还蠢到被人看见,真要坐牢也是天意,有什么好愁?最多给他家人一笔钱,叫兄弟们帮他照看一下。」
此话一出,林信和阿旗都不约而同抬起头来看我。
我大不自在,心情更糟,反直视着他们,「你们也是黑道混的,自然知道这一口好菜,就是准备配着牢饭吃的。现在却兔死狐悲,适应不过来?阿旗,难得连你也这么感性。」
「君悦,」林信冷着表情,硬邦邦说,「阿标是我们这边有资历的兄弟了。」
「那又如何?」
我不在乎。
别说什么狼眼标,就算眼前的林信、阿旗,我都不在乎。
而我在乎的那唯一一个,和另一人去了爬山游玩。
为了什么,我要又惊又怕地被唬上车,处理这些离我很远的血腥和死亡?
「君悦少爷,罪名一旦成立,阿标会被判无期徒刑。」
或者安燃是对的,我不但任性,而且确实自私。
别人死活,咎由自取,与我何干?
「我不管他有什么资历,反正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一人做事,就应该一人当。希望他以后在监狱里收敛脾气,不要再惹是非。」我咬牙,说得无情无义,没心没肝。
「你就不担心他会用安老大来换自己的自由?」
我一惊,「林信,你说什么?」
林信说,「阿标如果知道自己要坐一辈子牢,作为交换,说不定会转做警方证人,指证安老大。」
「安燃?」我问,「他有什么本事,能够指证安燃?」
「君悦,阿标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他有这个本事。」林信斟酌了用词,试图用和缓的语气,「有一次安老大办事时,打伤了一个人,阿标亲眼看到。」
阿旗说,「安老大一向谨慎,很少亲自办事的,不过偏偏那一次,阿标就跟在安老大身边。」
林信叹气,「我挺担心。这事来得太蹊跷,好像设计好似的,如果是宁舒暗地里策划的,那么他的目标不是阿标,而是安老大。当然,阿标未必就一定会背叛,不过人非圣贤,谁面对无期徒刑,都会想抓一根救命稻草。」
阿旗木着脸,幽幽盯着我,说,「君悦少爷,你知道,安老大是绝不能再回监狱去的。虽然只是伤人案,判起来刑期不会太长,但对于安老大来说,在那地方待一天,也不如死了干净。」
如一阵阴风掠过,所有毛孔都倒竖了。
我打个冷颤。
不可以。
安燃不可以再回监狱。
我不敢去想他曾在监狱遭遇过什么,每次企图触及那一点,神经就如铁石划过玻璃般,回荡刺耳令人发怵的尖叫。
我不敢问,却很清楚,安燃绝不能重回监狱。
我惨白着脸,「我该怎么做?」
林信说,「宁舒这招虽然阴毒,不过如意算盘不一定打得响。事情是从阿标处带起来的,只要阿标的案子不成立,他不用坐牢,自然不会和警方配合。这方面,我们在外面可以帮帮阿标。」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林信的意思,我再笨也明白几分,转头去看阿旗。
果然阿旗说,「事情一传过来,我们已经把消息都散出去了,务必把这案子的证人翻出来。摆平了证人,翻了口供,阿标的案子就能摆平。」
我问,「如果摆平不了呢?」
林信淡淡说,「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摆平不了的。真遇上不肯翻口的,可以让他永远闭嘴。」
我默然,低声问,「你真打算这样?」
「这也只是没选择时的路,目前还不用这样。」林信加了一句,「何况,君悦,如果事情真到那一步,我也会等你点头才动手。毕竟,现在你才是做主的那个。」
林信最后那一句,如石头沉甸甸压在我心头,那个分量,和往日的沉重完全不同。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只是当做主的那个,我不知会是这样叫人难受的差事。
做再多的心理准备,也是无用。
我依旧,惊惶绝望,像自己才是等待判决的那个,只求那证人是个胆小贪财之人,心甘情愿发一笔小财,用黑钱掩盖自己看到的真相。
到了公司,我基本都在发呆,心里都被这件事情装满了。
如果处理这事的是安燃,一定胜我百倍。
我电话安燃,他的手机却在关机状态。
拨了十几次后,我气得扔电话砸窗。
这天大要命的事发生,我心急如燎,安燃此刻,却正和一个莫名其妙的混蛋悠闲渡着快乐时光。
这事实,令人愤怒,又沮丧。
我在办公室中,被刺伤的野兽般来回徘徊,等待。
等待有关证人的消息,等待联系上安燃。
非常焦急,却又隐隐约约,极害怕等到结果。
我害怕那证人真的铁骨铮铮,无从收买,更害怕拨通安燃手机的一瞬,听见成宫亮传来的笑声。
那是极让人痛苦的时刻,莫测的噩运笼罩在头顶,无数爪子慢慢挠着心窝,我好怕。
越害怕,越忍不住去想,如果事情到了绝路,安燃要坐牢,怎么办?
如果安燃回到那个地方,被人折磨,怎么办?
如果我失去安燃……
不行,我不可以失去安燃。
只是设想,就已经痛到疯了。
勉强等到下午,安燃的手机还是关着的,连阿旗和林信都没有露面,他们本来说,一旦有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办公室已经承载不下我太疯狂自虐的想象,夕阳露面之时,我跌跌撞撞,冲出办公室,大声喝命备车回别墅。
但,安燃却不在。
我随手抓住一个手下,「安燃呢?为什么还没回来?」
「安老大早上出去的时候,没有留口信说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电话过来。」
「他为什么还没回来?」
那手下被问得不知所措,「君悦少爷,这……我不知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被我抓住的那个满额冷汗,恐怕他也明白,再一直回答不知道三字,只会让我发毛。
他说,「我现在就发散兄弟去找一下……」
「不用!」我失控般地大吼,「用不着!叫他别回来!叫他滚!」
我赶走所有人,在空荡荡的大房里颓然痛哭。
安燃没回来。
我知道,他正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对那人笑着,不经意的,唇角一扬,就是一个宠溺又带着无奈的笑容。
如此珍贵的笑容,一个接一个,他已不吝啬地给了一个陌生人。
我恨他!
若安燃此刻在我面前,我会像疯子一样对他咆哮,不啻用最恶毒的话来刺伤他。
只是即使如此,我仍不能不为他担忧,安燃可能要入狱的阴影,网一样黏在我身上,腐蚀入肌肤。
我只能一遍遍地想,一遍遍地恐惧。
寒气渗入每一个毛孔,我面对的不是绝对黑暗,而是仅有一支小烛的黑洞,眼睁睁看着,烛光微弱不堪,却还要被冷风吹得闪烁明灭,可能下一秒就熄。
那光亮随时会熄灭,绝望将永远覆顶的下一秒,把神经扯到几乎裂断。
那感觉,才叫恐惧。
我在房里来来回回徘徊,流出的汗,尽是冷汗,于是又把自己藏到床上,在被子紧紧抱着双膝,双重的软被覆着全身,还是冷。
天,天,求你让安燃快点回来。
我不要失去他。
求你让他在我眼前,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永不离我眼前。
我不断祈祷,足有千万遍。
终于,房门被人扭动门把,才推开一条细缝,我已经从床上猛跳起来。
「安燃!安燃!」
我扑过去,紧紧抱住进门的安燃,「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
「安燃,出事了,有一个叫阿标,有人命官司,警察有证人……安燃,他要是转成警方证人,那就糟了!安燃,你是不是真的被他看见过什么?……安燃!这事你一定要过问!」
我急速地半喊半叫,语无伦次,说完这番话,才发觉自己呼吸紊乱到极点,脸上已满是湿漉。
「安燃,怎么办?」我追问,「你说啊,怎么办?」
不知安燃今天是否真的有爬山。
身上穿着休闲服,气味却干净得彷佛没有出过一滴汗。
安燃问,「君悦,你打算怎么办?」
我慌张地回答,「本来杀人偿命,我是不想管的,让警察判他好了,最多我们尽一下人事。可是现在那案子有证人,而且那个阿标又刚好和你……」
「杀人偿命,很好。」
我愕然,「安燃,你这话什么意思?」
安燃笑笑,「就是很好的意思。不愧是何家后人,多少也有点根基,事情按照道理来办,不能勉强的时候,就不要强自插手。你说的很对。」
我在房里伤心焦虑,几乎熬成苦汁,他却清清爽爽,轻松自如。
我气急,「什么很对?他如果被判无期,难道不牵连到你。」
安燃气定神闲,「那又如何?」
我窒住,半晌讷讷道,「安燃,这样,你会又被抓进监狱。」
「和你无关。」
「什么?」我不敢置信。
「和你无关。」
我几乎吐血,却还要忍气吞声和他说,「安燃,你不要这样,现在,现在并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玩什么游戏?」安燃冷漠地打量我,「君晚,你觉得我这人,注定一辈子心血都要用在你身上?你觉得我的命,一辈子都是属于你的?」
「不是……不是……」
安燃说,「没错,我从前进监狱,是为了你。不过,」
他说,「不过,并不代表我还会为了你,再进一次监狱。」
我简直张口结舌。
这人强词夺理,不可理喻,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他竟不知我在为他担心?
我又气又恼,「好,安燃,我已经很明白了。」
我悻悻,「就算你这一次被人抓进去,也绝不是为了我。我明白,你现在不过要和我撇清关系,是不是?」
「是。」
这样斩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