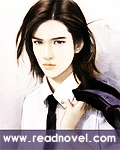并非阳光-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
这样斩钉截铁,我当场僵住。
安燃低声说,「君悦,别为我做什么事情。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反来欠你一个人情。」
我咬牙,「你到了那里,能活得下去?」
他说,「我的命,我的人生,爱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
我顿时无法做声,半晌,骤然放声痛哭。
报复,他在报复!
用我昔日的话,报复今时的我。
但,太不公平。
我的命,我的人生,爱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
这怎么一样?
何君悦不过是爱玩了点,多喝了点,让身体消瘦一点罢了,我不曾要绝自己的命。
安燃,你却是存心害死自己,狠心到要让我眼睁睁失去你。
我大哭,「安燃,我知错了,求你不要这样。」
你如此恨我,竟恨到连自己也不珍惜。
我紧抱他铁一样铸就的身躯,伤心地察觉着中空处令人魂魄分散的绝望。
我说,「安燃,我不知道你这样恨我。」
我哭着说,「原来你这样恨我……」
伤到深处,不速之客居然闯了进来·
「安燃,」成宫亮抱着枕头和一床迭得方正的小被,彷佛理所当然地走进来,「我今晚可以睡这里吗?刚好,你这里还有书……」进了门,猛然停下说话,好奇的看着我们。
我像被什么狠狠椎到痛处,彻底爆发。
「滚!」我冲过去,不顾仪态地朝他大喝,「你是什么东西?这样登堂入室?这是你能够进来的地方?我受够了!给我滚!」
成宫亮看着大失仪态的我,黑亮的眼睛并无怯意,反而,他立即狡黠地把眼珠转向安燃的方向,挤出一个乞求援助的表情,「安燃……」
「闭嘴!」我怒不可遏,扑上去卡住他的喉咙,「安燃是你叫的吗?是你叫的吗?你知道我是谁?你听过何家的君悦少爷吗?你知道我有多少手下吗?你这样的货色,来一百个,我捏死一百个!一百个!」
废物!
一百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宫亮,也斗不过一个何君悦。
有个当医生的爹地就自以为天下他是第一可笑!
他见识过血吗?他见过死亡吗?他试过把匕首刺入自己的胸膛吗?
他尝过,我那么血泪浇成的恨和热爱?
没有!
他凭什么来插上一手?
「凭什么?凭什么!」
我卡着他细嫩的脖子,像捏着一只可恶的小鸡,看着他的脸由红转青、满眼惊恐。
安燃走过来,抓着我的手腕,往命门上一捏。
「呜……」痛得我闷哼一声,不得不松手。
我悲伤地看着他,「安燃,你帮他?」
我捧着自己作痛的手腕,凄然看他,「你为什么帮他,安燃?」泪眼婆娑。
「安燃,好痛。」成宫亮捂着印上淤青的喉咙,逃入安燃怀里,声声哀叫,「好痛,我的喉咙好像被捏碎了。安燃,你看看我的脖子,他刚刚是不是存心按在我的大动脉上?」
安燃没做声。
我伤心至此,挨在他怀里哭诉的,却是另一个人。
好绝望。
我惨笑,「安燃,你真的帮他?」
安燃冷静得令人匪夷所思。
他的目光如镇定剂,静静盯着你,就能让你从极高温往下降,降到不冉有任何温度,只觉得冷。
安燃说,「君悦,你这人一向缺点多多,不过,如果有一个让我喜欢的地方,那就是,你手上从不沾血。」
我彷佛被冻住。
安燃淡淡说,「如果说我帮了谁,那么,我刚刚帮的是你。」
安燃说,「我阻止了你,没让你染上血腥,失去你身上最后一点可爱之处。」
「不过,」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从今以后,你要怎么做,由你自己做主了。」
我不要自己做主!
我摇头,「安燃,你说谎。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问,「为什么你要把公司交给我?」
然后自问自答,「因为你想看看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你要我站起来,也为保护而努力一次。」
我发誓,「安燃,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为了你,我什么都改,再难再苦的一事,我都能面对。」
「为什么我要把公司交给你?」安燃啼笑皆非,叹一声,怜悯地看着我。
我心寒。
他那种怜悯的眼神,是我心头大忌。
这表示他深深明白,自己即将说出的话,会把我打进地狱。
「因为这是你向我要的。」安燃把还在呜咽的成宫亮搂在怀里,对我微笑,「现在你有权有势,有公司有大批手下,叱咤风云,人人羡慕,有什么不好?」
我拼命摇头,「不,不,我什么都没有!根本就一无所有!」
安燃问,「君悦,你怎会一无所有?」
他说,「今非昔比,你什么都得到了,应该知足。」
我一直被撕扯的心脏,忽然发出轻微的响声,裂出无数细纹。
而血,从这些细纹中,一点,一点,都渗出来。
向下滴。
安燃,安燃。
他说的话,我常当耳边风。
我说的话,每个字,他都彷佛用刀,刻在自己心上。
如今方知,我的口不择言,每个字,对他都是惨痛一刀。
到底有多少次,我这样不断的,不断的,把他伤过一次,再伤一次。
「安燃,」我全身力气都被抽光了,颓然站着,惨笑,「原来我对你这样不好。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安燃说,「不用道歉,君悦。」
他亦苦笑,「你所作所为,我已经习惯很久了。」
我们彼此凝望着。
真让人心痛,这样的凝望,我以为自己还能有机会。
但原来真的,并没有永远的下一次。
还能用。
下一秒,液晶屏幕上出现体重数字。
我张大湿润的眼睛,看得那屏幕入神。
失去了那么多,我差点以为,上面出现的会是负数。
但这秤却显示,此刻情况,并非如此。
我茫然,走下去,又站上来。
再走下去,再站上来。
不可能,我浑身都是空的,像被蛀空了心的树干,但为什么,这上面的数字,硬生生告诉我,何君悦还是过去的何君悦,没有失掉哪怕一两。
骗人,骗人!
一定有,一定失去了,我明明感觉到,明明失去了。
我命中最珍贵的唯一。
我不断的上去,下去.,一次又一次,不肯死心。
骤然,找到答案似的停下来。
原来如此。
我凄绝地看着那液晶显示,终于发现真相。
那上面不见了的,是安燃的重量。
他再不会抱着我,静静站上这里,称出何君悦和他,在一起有多重。
这就是,我所失去的,已经失去的。
安燃的,安燃的,重量。
我明白过来。
哭死过去。
第五章
我失去了如此珍贵的,没一人一言安慰。
更可悲是,事情糟到如此地步,却还没去到最尽处,还能继续惨重下去。
我孤零零在清冷小房中哭死过去,清晨,又被阿旗摇醒过来。
我睁开红肿疼痛的眼,往上看,「阿旗?」
「君悦少爷,有消息了。」
我吃了一惊,弹簧般坐直起来。
阿旗说,「我们运气算不错,宁舒虽然不安好心,不过警方似乎并不知道事情始末,并没把这事看得太要紧。证人也只是暂时转了去酒店,以策安全。」
我松一口气,「幸好。」
若证人受到警方严密保护,甚至藏去安全屋,要对他们下功夫,可就麻烦多了。
阿旗神色比昨天轻松多了,点头道,「地址查出来,剩下的事林信会办,有钱能使鬼推磨,大笔钱砸下来,不怕那证人不识趣,也要惦量一下自己够不够分量惹这桩事。就算他不爱钱,总不会不爱自己的命吧。」
我心事沉重,偏被他一言带起,兴奋之色顿去,满面黯然。
阿旗彷佛也察觉出来,静了一会,才问,「君悦少爷,昨天在这里过夜?」最简单平常的语气,听不出一点异常。
不见我答复,他便轻描淡写说,「这房间虽然小,不过方位很好,南。如果君悦少爷想在这里小歇几天,今晚我就叫人换一床新枕被过来。」
他说,「这里的枕被,自从君悦少爷用过后,安老大都不许人随便换走。」
我掉头去看床上。
真的,一仔细瞧,都是熟悉的被色。我用过的。
我问阿旗,「安燃现在在大房?成宫亮昨晚和他一起?」
阿旗蹙眉,「我昨晚已知道君悦少爷暂换了房间,今天接到林信通知就直接过来了。大房那边还没有去看过。不然我现在过去看看找个人问。」
我摇头,「不用了。」
长长的,吐一口气。
阿旗问,「今天回公司吗?」
我点头。
不回公司,能去哪里?
那曾和安燃无数次相拥入睡的大房间,已不是我能去的地方了。
我回到娱乐中心,仍旧的前呼后拥,气势过人。
纯白西装,笔挺烫贴,在众人交错的羡慕视线中,被奉承得更为尊贵。
没人知道,我一无所有。
这副好皮囊,盛满了一加仑一加仑,无止无尽的,艰难,和绝望。
即使如此,我却不得不继续昂头挺胸,这样走下去。
无他,因为已没有什么可以支撑了。
我想自己唯一能做的,是把这要命的事对付过去,并不奢望这样能挽回安燃,我只是单纯的残留着那么一点意识。
我必须,必须,找到一件,能让自己更苦更苦的苦差。
这是和天赌气般的自毁,人就是这样,有一点痛,你寻尽各种方法舒缓,但若痛到极点,就会发泄般,咬自己的手,咬自己的唇。
不为得到解救,只为表达绝望。
办公室内,我不断找事情,没事情,就看那些永远看不明白的书,一边看,一边等待林信消息。
按捺着,不向任何人过问安燃。
他在别墅?或出门了?
正和成宫亮谈笑,还是独自倚在沙发侧边,静静看书?
昨晚,我心碎着后退,转身那刹,他到底,有没有看着我的背影消失?
很多很多问题,浮上心湖,如一个个充满气的倔强皮球,带着暗哑的血色,被按下去,又浮上来,此起彼伏,从不曾真正的沉下湖底。
但,我咬牙,忍着不问。
装给自己看,我已经认输。
承认了,退出了,知错了。
道歉,转身,在寂寞房中沉痛反省,痛哭一场,就当它结束。
骗人!
骗自己。
行尸走肉般,到头来,却又被林信一个电话戳醒。
「不答应?」我拿着电话,惊讶过甚,忘了仪态地对着那头的林信大吼,「怎会不答应?林信,你到底办的什么事?我说过,他们要多少给多少!」
「君悦,他们不爱钱。」
林信的声音,镇定得可恨。
我切齿,「不爱钱?那他们爱不爱命?」
林信说,「他们很爱命。」
我说,「那就好,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法庭上如实作供。」
「什么?」
林信沉默后,说,「君悦,宁舒插手了。他放话出来,证人如果推翻口供,日后休想安生。」
潺潺冷汗,从脊背上冒出来。
林信说,「警方承诺提供保护,宁舒施加压力,要求的又是合理说出真相。君悦,换了你是证人,你也知道应该站哪边。」
「安燃,」我喃喃道,「当然是安燃。」
「君悦……」
我不知道林信还想说什么,猛地砸了桌上电话,把自己藏在空空软软的沙发里。
想念。
想念这有点粗糙,却又柔软的感觉。
它从我进驻娱乐中心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我却没有在上面舒适过一回。现在,却忽然深深的,深深想念起这被包裹的感觉。
陷在里面,拔不出来。
用不着拔出来。
一如昔日,只要顾着自己就好,哭泣哀求,伤心绝望,去爱或恨。
别把旁人生死交到我手上。
别逼我迎面对着一重一重巨浪,却连闭上眼睛的权力都没有。
我不想做任何人的保护伞,尤其是安燃。
那太沉重。
太难。
我保护不了!
林信在我甩了他的电话后,匆匆赶回,和阿旗一起来到办公室,看见我如受到惊吓的懦弱小兽,缩在沙发里,颤得毫无尊严。
「君悦,起来。」林信过来,把我从沙发中扶起来。
我恐惧起来,对他摇头,「林信,别这样。」
我求他,「不要又来说什么我要保护安燃的话,我做不到。你明白吗?我根本做不到。」
我哭着说,「我一无是处,我承认,我没用。林信,你帮帮我,你去救安燃。」
我仅存的力气都用在十指上,紧紧抓得他笔挺西装皱成一团,不顾颜面地恳求,「你比我有本事,一定可以解决这事。林信,安燃不可以坐牢,你一定要做到,我一直都信任你,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必须帮我这一次。」
「我帮不了。」
我僵住。
抬起哭红的眼,不敢置信,站在我面前,拒绝我的,会是林信。
我声音极低,「林信,你说什么?」几乎只有气从唇中出来。
极失望,极不相信地看他